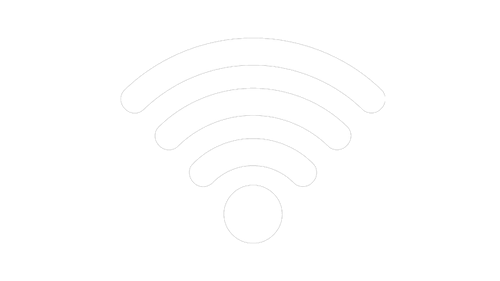聂元梓:一个造反派代表的潮起潮落
中国第一造反派,名扬四海。“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主笔聂元梓仍然活着(本文2001年撰——编者注聂元梓今年已届八旬。提及1966年“文革”初起之时,她那冲击北京大学领导层及北京市委的一幕,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组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新。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支持,在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 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宣布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京各大高校。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同走下舞台,丧失了领导各自院校“文革”运动的权限。 聂元梓早年经...
中国第一造反派,名扬四海。“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主笔聂元梓仍然活着(本文2001年撰——编者注聂元梓今年已届八旬。提及1966年“文革”初起之时,她那冲击北京大学领导层及北京市委的一幕,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组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新。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支持,在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
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宣布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京各大高校。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同走下舞台,丧失了领导各自院校“文革”运动的权限。
聂元梓早年经历
聂元梓出身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其父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是滑县共产党的先行者、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聂真生于1907年,今年94岁(2001年)思维清晰,记忆犹存,他在离休之际,身为正部级高级官员。
聂氏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最小的,也是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的一个。聂元梓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除二哥是未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外,其他都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哥参与领导的滑县共产党县委创立后,在其父母支持掩护和物资支援下,曾长期在家办公。抗战开始,他家更成了过往八路军人员的家,不仅管住宿、吃饭、医疗,还有经费的支援。敌人占据家乡后,母亲曾遭逮捕,在狱中坚强不屈。随后父母都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耳濡目染之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只念了两年初中的少年聂元梓,便跟随二姐和姐夫,到了山西太原,在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创办的学兵队,并接受了严格的军训。当年八月,她正式踏入了工作岗位。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首次投身的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其领导人是资历深厚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
彼时,王世英身为北方局情报部长,深感迫切需创办一份地下情报刊物,以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在战时及时提供情报支持。他精选刘贯一担任该刊物的主编,并指派聂家姐妹协助刘贯一的工作。三人共同居于一个幽静的小院,宛如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作“家庭”。刘贯一化装成“姐夫”,与聂元梓的姐姐同行,共同搜集情报。而聂元梓则留守家中,负责打理事务,将精心编撰的文稿刻录于钢板上,并书写蜡纸,进而进行印刷。这份油印的小型情报刊物发行量极低,总计仅印制5份,专供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德怀)五位领导人参阅。
1953年,聂元梓已被评定为12级干部,跻身党的较高层领导干部行列。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的家庭生活遭遇了波折。她的伴侣因生活作风问题犯了错误。彼时,她已是一位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一变故对她的情绪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最终,他们不得不办理了离婚手续。怀着改变环境的愿望,聂元梓决定前往北京寻求新的工作机会。
1959年,她将孩子们分别安置在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经过她大哥聂真向北大校长陆平介绍,聂元梓于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
文革初红极一时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牵头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使聂元梓成为毛泽东亲自支持、树立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一个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帜。自那日起,聂元梓在“文革”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已然确定。
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聂元梓着实有点儿受宠若惊。那张大字报结尾,她添加的一小段文字和“保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正是她心里的话。
1966年8月之初,中共中央举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该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聂元梓荣获殊荣,她与北大教员张恩慈、杨克明一起列席此会,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要求他们回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当工作组被派遣至各大高校展开行动,在这五十多天的时间里,这被称作“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意图打压无产阶级气势如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
如此一来,经历工作组失势和北大校园的空白期后,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之际,便是由当时负责高校运动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筹备机构。9月11日,经过一番选举,她光荣地担任了“校文革”的主任一职。
1968年命运突变
1967年夏末,聂元梓初次感受到“文革”前途的扑朔迷离,她的热情与信心也随之消磨殆尽。在她看来,众多老干部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而被打压,群众组织也陷入分裂,局势混乱至极,似乎“文革”已经注定走向了败局。然而,她依旧坚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受到了某些人的破坏”,她所指的,正是“中央文革”内部的一众成员和谢富治。
于是,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教诲!毛主席未曾让你退位,你又怎能擅自离场呢?”
即便如此,聂元梓在8月份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总理亲自出席之际,毅然提出了辞职的申请,并进一步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倡议。江青她首先起身发表反对意见。她严肃地说道:“先前你力保‘校文革’,而今对方发起攻势,你却要求解散‘校文革’,你的立场动摇了,这是不行的!”
聂元梓在延安与江青相识,但彼此并不熟。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元梓之后,某天江青邀聂元梓上她住地共进晚餐。那回江青真是向她交心,讲了刘少奇夫妇的坏话,讲了外界所不知的她搞京剧改革彭真如何“刁难”她的情况。江青意图通过此举,以心换心,将聂元梓培养成自己的心腹与得力助手。她特地叮嘱聂元梓,今后若有要事,可直接拨打电话向她求助。
那么,聂元梓又是如何行事的呢?她创立了“校文革”组织,一旦遇到事情,她会依照组织流程,直接向当时负责高校“文革”工作的“文革小组”另一位副组长王任重。这标志着她与江青关系破裂的开端。随后,江青成功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她指派手下将聂元梓带到“中央文革”记者站,进行变相软禁达数日之久,并要求聂元梓交出在成立“校文革”期间的所有与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在1967年,聂元梓虽辞去职务,却未得到批准。至1968年,她所领航的北京大学“校文革”运动仍旧秉持“消除隐患”的原则,积极反对康生和谢富治。聂元梓及其团队坚定地持续着这一立场。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高层人士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他们很快便失去了自由。经过审查、批斗、禁闭以及劳改等经历,长达五年的时间,到了1973年3月,聂元梓被冠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党籍被开除,并被实行监督劳动。在“四人帮”掌权期间,聂元梓被监管长达八年之久。
反革命罪判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击败。
1977年2月14日,北京大学党委传达了北京市委负责人的指示精神,其中特别强调了几个“不能翻”的原则:“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容翻案,对于前17年的历史亦不可颠覆。(1949-1966)所谓的“两个估计”系指不可翻译的内容,而文末的“不能翻”特指“聂(元梓)案”不得译介。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聂元梓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京大学党委正式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聂元梓应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予以开除党籍,并提议按照法律进行惩处”。此举标志着聂元梓将面临法律的严惩。紧接着,在同年4月19日,她被正式逮捕,并在看守所内度过长达5年的羁押期。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决如下:对被告人聂元梓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四年。”
聂元梓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满,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受理上诉后,指示看守所通知聂元梓准备提交上诉的补充材料。待聂元梓完成上诉补充材料的撰写,高级法院已委托中级法院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送达。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押送至北京市远郊的一所监狱接受服刑。负责押送她的看守向监狱的管理人员简要说明了情况:“这位女犯人,总体表现尚可,唯独不肯认罪。”
入狱不久,聂元梓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过失源自在执行毛主席指示及党中央路线过程中产生的偏差。然而,我并未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策划的反革命阴谋,意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已明确指出,他们的阴谋行为与本人毫无瓜葛。我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派系联系,也未实施过任何打、砸、抢行为。既然我没有触犯刑律,理应不受《刑法》的惩处。”
“在‘文革’初期,我确实犯下了错误。对此,我将向党持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承诺彻底进行改正。然而,我的问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能确保从中吸取教训,进而达到既教育犯错者,又启迪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目的。”
“我深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确立的领导方针是无比正确的,并且坚信我的个人问题也将得到妥善解决。我恳请党中央能够尽快公正地处理我的问题,以免让我的同志及其家人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承受这无法洗刷的冤屈。”
1984年,聂元梓身患多种疾病,病情亦日趋严重,年末之际,她被安排返回北京接受“保外就医”。次年11月,监狱方面通知聂元梓,她已被裁定“假释”。到了1987年,她终于获得了选民证。
聂元梓深觉自己被判入狱是不公,出狱后病情略有改善,她便开始撰写申诉材料,并积极了解案件审理的细节。与此同时,她的子女也持续向法院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
文革导致严重灾难。聂元梓是造反象征。象征着积极追随极“左”错误路线的典型,“犯上作乱”的标志。我们绝不能再容忍破坏社会稳定、扰乱国家、颠覆政权的行为发生,这是历史所给予的深刻教训。对这类造反者实施惩戒,实乃必然之举。

聂元梓晚年隐居,著回忆录
晚景凄凉,沉默矣。
数载之前,在与聂元梓结识之先,我已先一步与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相识。闲聊中得知,他的妹妹是聂元梓,聂真向我透露,他的妹妹已刑满释放,并取了一个他人为她取的化名,投身于商海。鉴于我对“文革”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便决定拜访聂元梓。
聂元梓的住址中,附带着一个“宫”字。我出于个人的臆测,心想聂元梓或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定是住在“宫”字号的高级宾馆里,从事着规模宏大的商业活动。然而,见面时我大吃一惊,原来所谓的“宫”不过是她亲戚所在单位宿舍楼的一个普通地名。她的住所仅有两间狭小房间,房屋亦显得颇为陈旧。聂元梓解释说,她从事商业活动只是为了找些事情做,然而数年过去,她并未从中获利,反而公共汽车费和电话费的开销颇多。她进一步透露,出狱后她面临无生活费、无医药费、无住房的困境。近年来,她全靠亲友的接济,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
聂元梓的神情似乎显得颇为漫不经心。她提及,出狱后她险些丧命,但她不愿就此离世,又无力负担昂贵的药物,便凭借着顽强的意志,通过锻炼身体和腿脚,终于从病榻上站立起来。“文革”这场风暴已肆虐了近30年,她身负“反革命”的罪名,饱受监管、劳改之苦,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入狱,但那些最为艰难的时光她终究是挺了过来。
在这十数年间,聂元梓的生活一直颠沛流离,缺医少药,不得安宁。自1999年起,得益于政府的补贴,她的医疗得到了保障,生活得以相对稳定。然而,住房问题仍悬而未决,暂未找到解决办法。
如今,聂元梓的身材略显丰腴,身患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其中,腰椎骨的错位是在20世纪70年代,她在江西鲤鱼洲挖河泥时不慎摔倒,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未能及时得到治疗而留下的后遗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第五腰椎骨错位已超过一半,时常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若不及时治疗,存在瘫痪的风险。然而,由于心脏病的原因,她不能轻易接受手术。她每天上午步行,乘坐公交车前往医院打针、取药,她认为这样的活动对锻炼身体大有裨益,心态总体保持平静。她的日常生活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的生活方式。日常饮食以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为主,均由她亲自采购和烹制。若有客人来访,她会额外准备一些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呈现出一派浓郁的河南乡土风味。
聂元梓已不再提及自己“案件”的平反与更正。她仅言:“且信史为鉴。”